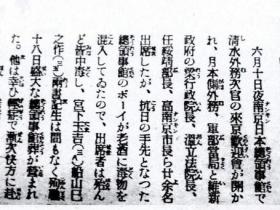以今天的眼光看,秦始皇固然有残酷无情的一面,也有超前的眼光与惊人的想象力。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出现在距离纸张发明尚有300多年的时代,正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赞叹,在基督诞生之前,中华帝国就显示了与20世纪超级国家的相似之处。

作者:朱步冲
季风与黄河造就的契机
为何中国的首次统一大业需要由一个身处文明核心区域之外的政权来完成?我们就需要把目光投向孕育这古老文明的土地本身的特征:中国地区属东亚季风区,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从菲律宾太平洋吹来的热带季风必须与西北之高压冷空气会合,才能冷凝为雨。如果两种气流不幸错过,则为旱灾,而在某地会合频繁,则会产生涝灾。古人缺乏这种气候常识,只好以粗浅的经验总结灾难规律,《史记·货殖列传》上就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说法。不仅如此,降雨量如果按地形分布,则有一条13英寸等雨线横亘中国大陆,这大致就是日后秦长城的构筑路线,宣布此乃农业与畜牧生产方式的天然界限。灾年一到,北方游牧民族就会定期南下掠食,早在战国时代,赵、燕、魏等国已经分别修筑长城加以抵御,客观上暴露出这种国防事务亟须统一指挥管理的必要性。
除了季风性的降雨天气,横亘中国、定期泛滥的黄河也是促进中国统一的另一内驱力。《孟子》中提到“理水”就有11次之多。而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与生产。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的“葵丘之盟”,即提出“无曲防,无遏籴”的号召,意为各国不许兴修妨碍彼此灌溉运输的水利设施,在荒年不能阻止粮食流通。汉书中魏国人李悝即指出灾害频繁之下小农生产的脆弱性:一家五口,授田100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产量即是150石,假使税率为10%,再减去全年口粮90石,一家每年余粮不过45石,折钱1350文,但是每年春秋乡间祭祀要花费300文,再加上每人衣裳开销300文,已经出现450文之巨大赤字,尚且不算丧葬婚娶等其他用钱之处。何况天灾频繁,米价极不稳定,所谓“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意即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在这种严酷情况下,必须以强大的中枢统一规划调度,才能使小农达到丰年有余粮,荒年不致辗转于沟壑的最低生存标准。所以诸侯掌握领土与人口越多,应付灾年才能长袖善舞,也让吞并战争有了内在的原动力。《吕氏春秋·爱士》记载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听从百里奚之言,借粮于晋。然而次年秦国大旱,晋惠公不救,于是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惠公被俘。所以综观春秋以降,客观上也需要一个坐镇上游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取代羸弱的周天子,才能充分动员资源,兴修水利,稳定粮食价格,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在旱灾年份的定期入侵,从而保证稳定。虽然直到战国初期,秦仍然被六国看做化外之民。然而崔瑞德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指出,包括秦在内,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以西陲为基地的政权最终实现统一的现象,就是因为相对于中原,这片土地具备战略上的绝对优势,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四方被散关、函谷关、武关与临晋关保卫,西北有黄河之险,南有秦岭与巴山之固。易守难攻,三面都是较之中原各国落后黯弱的少数民族部落,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称为“九州膏腴”。这一切都可以使秦人无后顾之忧,专心东进。
法家与军国主义——从“战胜”到“制胜”
历史决定了秦人的命运,而他们也几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扩张。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在制度层面上,秦国的专制君权早就具备了优于山东六国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力,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例如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就以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三位著名勇士虎、奄息、仲行,由此留下了《诗·秦风·黄鸟》中“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诗句。秦与三晋比邻,民风习俗相近,当战国初期各国兴起变法之风时,秦人也立刻从中获益。商鞅曾受李悝《法经》六篇,秦的田制、阡陌制度,也源自赵、魏、韩。在秦国借以富强的众多客卿中,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商鞅之师尸佼,也是晋人。商鞅建立的军功爵制,最终被定型为20等,有爵者可以享受多种特权,免除徭役、减刑抵罪、豢养门客、穿着华服。虽然三晋、齐、燕、楚等国也存在各种爵制,但在严密程度与军功紧密结合程度上,都不如秦制,正如商鞅所说:“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的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在荀子看来,“法”作为一种纯粹,量化,直接服务于富国强兵目的政治规范,就应当从“礼”这个杂糅了民俗、道德、仪典、政制、宗教的混合物中脱胎而出。而法家的“非道德主义”则主张国家的“霸道”与秩序,强权,管理机器精密的运转,本身就是其存在的目的。集儒法两家宗师身份于一身,高足囊括韩非、李斯的荀子,应当被看做是秦国坚定走上法家政治道路的始作俑者。他的著述丰富且细致:《富国》、《君道》等篇旨在治道政略,论吏治选官有《臣道》、《致士》,关于兵制军略,则有《议兵》。所以刘歆在《七略》里同时将荀子列为儒家与兵家,荀子主张以“礼”为治之始,而“法”为治之端,统治阶级由掌握礼乐、仁义的士大夫和从事技术职能的官吏组成。算是汉代以降,中国历代王朝“儒表法里”统治意识形态的先驱人物,所以两千年后,谭嗣同才会发出“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的感叹。
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崛起在西方,残酷的兼并战争就在所难免。《战国策·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在军事技术相对平衡的冷兵器时代,动员力与数量在长期争霸中占据决定性作用。闻名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上千件兵器除少数铁箭镞外,大部分全系青铜铸造,而南方的楚国与北方的燕国已经在大量使用铁兵器,然而秦国的敌人们并没有获取相应的战争优势,《荀子·议兵》中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根据马非百《秦集史》中“首功表”所列,从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王政十三年(前341~前234)这107年里,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的仅4次。秦军共斩首敌军约167.8万人。对于文献记载的战国晚期秦军斩首敌军之数,许多西方学者,比如《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编著者崔瑞德,都以为有夸大之词。但秦人在战争中的残酷无情和崇尚首功,则是毫无疑问的,《商君书》言秦“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秦律·封诊式》中甚至记载过士兵之间为争夺敌人首级而私斗,或以阵亡战友之首级上呈企图冒功领赏的案件。
尽管在作战中残酷无比,秦军却是一支组织等级高度严密的武装力量。为这支庞大军队的武功提供支援的,就是秦在商鞅变法后100多年中逐渐发展出的缜密细致的官僚行政机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秦简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管中窥豹。
睡虎地云梦秦简中所见秦律,已经有30多种,然而这些显然还不是秦律的全部。从内容上看,其缜密苛刻,覆盖面之全,很难想象这是2200年前制订的。坟墓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喜”的官员,出生在秦昭王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62年,秦始皇出生前两个年头。他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是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器上的一个无名且勤勉的零件,正如日本学者米刃山明所说,“战国时期政权的官僚法制化和社会军事化密切相关,军事技术官僚取代世袭贵族成为社会等级的主干”。“喜”,大约活了45年左右,曾经参加过三次秦国讨伐六国的战争,和千千万万忠于职守的同僚一样,他毕生都在完成这个企图把生产、社会运转与管理的各个细部都纳入法律量化管理范围的任务。
从这些用兔毛笔蘸松油墨撰写的记录中,我们得知秦法详尽规定了每个士兵、农民、官吏的职责:仓库漏水导致粮食霉烂,损失在百石以下,主管官员“仓啬夫”就要受到申斥,百石到千石之内,就要缴纳一副甲胄作为罚款。每年年底,所养耕牛能够肥壮的农业管理官员“田啬夫”将得到酒一壶,干肉十条,并免除下属养牛人30天徭役。每个制造兵器的工匠和监督者,都必须把名字和职务镌刻在自己的作品上,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则要受到逐级追究。
甚至连大秦军团中每个士兵的伙食标准也被仔细量化: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而二级爵位的上造就只有粗米一斗、菜羹一盘、盐二十二分之二升,至于普通士兵,则只能勉强果腹。很显然,秦国的“战之胜”是依靠它相对于六国的“制之胜”来实现的。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齐国首都临淄,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
“二世而亡”的帝国试验
虽然始皇本人在统一后下达的诏书中谦虚地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然而当日他肯定已经意识到,秦制将为统一后国君自由意志的行使提供了更大的“制度性空间”。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在秦政府的组织下接连展开,除了在首都咸阳修建的庞大宫殿和陵墓,北方宏伟的长城和深入南方的灵渠之外,不少于30万的罪犯与工匠开始修筑连接政治中心咸阳与关东政治中心洛阳的“驰道”。这条“中国最早意义上的高速公路”不仅是秦始皇数次出巡的必经之路,也是各地粮食贡赋与人力资源源源不断输入这个未来1000年内政治中心的主要渠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在公元前212年,修建了一条从咸阳至九原,途经甘泉、榆林的直道,与长城一样,它成为秦帝国抵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利器,一旦战事发生,来自内地的大军和给养就可以顺着这条最大坡度不超过10度的国防干线火速增援。不过就在直道仅仅修建完工一年后,它就充当了一场决定秦帝国命运的政变舞台——在秦始皇病逝于沙丘平台后,赵高与李斯命令载着始皇尸体的巡游车队沿直道由河北井陉北上,前往九原,先矫诏赐死毫不知情、驻守上郡的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然后再通过直道迅速返回咸阳拥立胡亥。100年后,直道终于在保卫大汉王朝的战争中第一次显示了它的作用——汉武帝时期,几乎每次对匈奴用兵,都是通过直道进行,从而成就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的赫赫声名。始皇又改黄河名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按照五德终始说,水德的特点是“阴……主刑杀,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按照这种抽象的超自然规律,各种器物必须以六为基数,“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表面上这种依赖神秘力量的作风与秦国法家政治的务实缜密性截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抽象道德礼仪制度的背后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考虑——秦始皇在统一后常常巡游各处,立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也就是将旧有六国互相竞争截流的水利工程拆除。尽管如此,这种超时代的政治统一,必定有管理技术不及之处,所以不得不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抽象理念作为弥补,从而使中枢权威合理化,进而加强上层对于下层之控制力。
然而,颠覆秦始皇伟大帝国的因素正潜伏在它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中。法家苦心孤诣制定的制度中,唯独缺少了官僚机构对于君权的制衡,因此对统治中枢的决策毫无折冲缓和。秦统一后,人口大约2000万,被征发造宫室坟墓150万人,驻守五岭50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之兵30万人,修筑长城大约50万人,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如此大规模急促地动用人力资源,造成了社会矛盾的骤然激化,然而秦帝国百年来统治的惯性,只能一味地用严刑峻法加以压制,造成了“赭衣半道,群盗满山”的局面。不仅如此,秦国官吏政治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对传统“礼治”的压抑,使得它遭遇来自关东六国遗民强烈的抵制。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几乎与秦孝公任用商鞅、使得秦走上法家政治之路的同时,齐威王却宣布臣子中能当面揭露自己过错的,给以上赏,上书劝谏者受中赏。而在公共场所发表政见,能最终被国君听闻者受下赏,齐国的城市居民“国人”可以与国君签订盟约,干预国政。足见秦与六国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陈胜吴广起义后,鲁国的儒生纷纷携带礼器前往投奔,孔子的九世孙孔甲更担任了陈胜政权的博士。秦国这种经过长期精密建构的法家文吏政治,尽管有很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它的单一狭窄性无法应付统一后关东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并做出自我调解,这正是为何它既能“鲸吞六合”,而又“二世而亡”的关键。如果脱除抽象的道德评价,那么始皇草创的王朝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激进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试验。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还需经过209年的试验与调整,才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终于构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进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