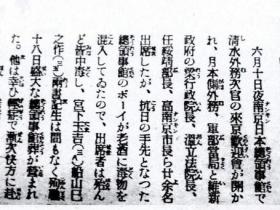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前后,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当时的吕氏乡约跟国家职役毫无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建构的乡党自治组织。

作者:吴钩
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初三,四川巴县孝里四甲有个村民到县衙告禀,他的禀词是这么说的:“蚁民(原文如此。清代巴县的平民在跟官府打交道时,要以“蚁民”自称,以示卑贱)叫做杨国材,父亲杨尔安原是孝里四甲的乡约长,一直兢兢业业办理公事,谁知不幸于今年九月十一日去世,蚁民本应代亡父承办公务,不敢渎禀。只是蚁民上无叔伯,下无兄弟,无法分身于公事,所以办过父丧之后,赶快前来衙门交还父亲的乡约长执照,请衙门注销父亲的名籍,另择乡约长。”杨国材还向县衙推荐了本甲名叫王介凡的富民,说他“不但殷实,且为人老成谙练,素行耿直”,非常适合当新一任的乡约长。
清代的乡约长,是社会基层组织——村社、里甲的负责人,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权力伸入乡村社会的行政末端,其职责为协助官府收税、管理乡村。谁家交税迟了,就由乡约长去催缴;谁家夫妻吵架闹离婚了,也请乡约长去调解;乡里来了什么形迹可疑的人物,乡约长也有责任向官府汇报;领导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由乡约长负责接待。总而言之,清代的乡约长的职责跟今日的村干部差不多。
杨国材告禀之后,很快发现官府并没有注销他亡父杨尔安的名籍,巴县衙门下发的一份各乡约承办公务的通知中,仍有杨尔安的名字——此时杨尔安已经身故一个多月了。所以十月二十三日,杨国材又跑了一趟县衙,请求官府注销父亲的名字,并请县太爷“即饬王介凡赴验给照,以便伊承领办公”。
巴县的知县批复:杨尔安既已身死,马上将乡约长之职安排给王介凡承充,县衙各个机关单位请及时更正名册。但十一月初三,王介凡前来衙门申诉,说不应该轮到他来当乡约长,因为他家兄弟已于乾隆十八年承充了三年乡约长,而且他现在又有病在身,实在不堪大任,“伏乞”老爷明鉴,另选贤达。县老爷很生气,批示:“遵照承充,毋得捏混推卸!”
这个收录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的故事,显示了清代乡约的尴尬处境。乡约长责任繁重,比如税粮收不上来,要由他们垫付;但又地位低下,形同职役,是给官府打杂当差的。所以,当时乡村中稍珍惜声誉的乡绅、耆老,都不愿意充任乡约长。而奸滑之徒,则抢着想当,因为乡约长虽是职役,但毕竟有点权力,这点权力如果运用得好,也是可以捞钱的。于是沦为国家权力末梢的乡约,品质越来越粗鄙,高士退避,流氓当道。
吕氏乡约的由来与乡党自治
然而,乡约刚诞生时并非如此。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前后,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当时的吕氏乡约跟国家职役毫无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建构的乡党自治组织。
吕大钧认为,在同一个乡里生活的乡党们,完全可以,也完全有必要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村社共同体,大家在共同体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个共同体就是“乡约”。
今天说起传统乡土社会的自治组织,许多人总是习惯地等同于宗族。其实不然,比之历史的丰富性,今人有许多误读。事实上,从宋代开始,富有社会关怀的士绅群体发起并领导了一轮又一轮的社会重建运动,不仅复兴了宗族,也创建了一系列跨宗族的社会自治组织。
北宋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以宗族公田的租金收入为全族成员提供丰厚的福利,成为宗族慈善组织的典范,运行了近一千年,是世界上维持时间最长的NGO之一。南宋人史浩成立的“乡曲义庄”仿效自范氏义庄,但它救济的范围跨越了宗族,为同一乡里的乡亲供应福利。
朱熹极力推广的社仓,是乡村自助机构,类似于农村小额低息扶贫贷款,处于青黄不接之际的穷人,均可以向社仓申请救济。由乡绅、富民、宗族兴建的义学,作为传统社会的免费教育机构,让当时最贫困的穷人子弟也有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所有这些各具功能的乡土组织,将传统的乡村社会联结成一个具备高度自治能力的有机体,像吕大钧这样的乡绅,则是组织乡党自治的灵魂人物。
吕大钧给蓝田乡约设计了一套优良的制度,并根据施行的实际效果加以修订。按蓝田乡约之制,凡一乡之人,都有权利加入乡约,入约与退约均凭自愿。乡约的领袖叫做“约正”,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由众人选举出德高望众、正直公道之人担任之。乡约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不以高下,依长少输次为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换,只要是入约的乡党,都有机会当上“值月”,管理乡约。也就是说,宋代的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入约的乡亲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
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举行乡饮酒礼。乡饮不仅是联络众人情感、维系乡约认同的仪式,更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因为聚会的时候,将根据入约之人近期的善行或恶行进行赏罚。约中众人有事,也可以在聚会上提出来,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显然,吕大钧创立的乡约,是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共同体,旨在促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自治秩序。其成立、运作的过程,均不需要官府插手,跟清代的乡约完全是两码事。
正因为吕氏乡约坚持独立、自发的民间自治属性,它在推行之初,遇到了一些阻力,包括吕大钧的兄长都反对搞什么乡党自治。他们对吕大钧说:你一个在野的士绅组织结社,容易被人误会为结党,引来朝廷猜疑。况且治理地方社会本是官府的事,你又何必掺乎呢?吕大钧回答说:士绅当造福乡里,何必要当了官才来行善事?如果什么事都由官府指示了才可以做,那“君子何必博学”?
乡约由自发向官府介入流变
乡约在宋代尚未普及推广,不过吕氏乡约的整套制度,经过朱熹的整理保存了下来。从明代中叶开始,在官方力量的推动下,乡约作为乡村基层组织,才在全国各地火热铺开:“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但乡约在获得推广的同时,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又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民间自发性与自治性。
晚明有个地方大员叫做吕坤,在他担任山西按察使、督抚期间,非常热心推行乡约,但他设计出来的乡约制度,已经跟宋代的乡约大不一样。
首先,宋代乡约的领导人是由一约之众选举出来的,政府全然不干预;“吕坤乡约”的约正虽然也由选举产生,但名单必须报送州县衙门备案,约正绩效如何,也由官府考核。
其次,宋代乡约可自由入约、退约;吕坤乡约则要求每户必须有一人入约,而家奴、佃户等低贱之民,则被剥夺了入约的资格。
再次,宋代乡约以自治的方式行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功能;吕坤乡约则需要接受官方的业务指导。吕坤要求乡约定期宣讲朱元璋的“圣谕六训”,又给各乡约发放统一格式的“格叶”,用来记录约众的品行,每年十二月,所有“格叶”装订成册,送州县官审查。
概言之,吕坤认为,“乡甲之约,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弹压操纵之权,全在有司”。
进入清代,官方对乡约的控制更加深入,乡约长很少由民选产生,大多由官府指定、委任;即使有经选举产生的乡约长,人选也必须报官同意。所有的乡约长,都必须获得州县衙门发给的“执照”,才可以履职。所履之职,也慢慢从以前的领导乡党自治,蜕变为替衙门办差。
用同治皇帝的话来说,“各直省州、县向有保长、乡约等名目,原为稽查保甲、承办差徭而设”。可以说,清代的乡约已经完全丧失了民间自发性与自治性。这便是四川巴县孝里四甲无人愿意承充乡约长的背景。清代巴县设有忠、孝、廉、节、仁、智、慈、祥、正、直十个里,每里下辖十个甲,每甲设若干乡约长,协助官府管理一甲公务。既是衙门委任,那么无论孝里四甲的富民王介凡多么不愿意当乡约长,官衙也不准他推诿。
直到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随着士绅精神的复活,民间社会的自治记忆也被唤醒,具有自发性与自治性的绅办乡约才得以复兴,其中尤以定县翟城村在乡绅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带领下的村自治最令人瞩目,翟城也成为清末民初公认的自治模范村。时人以为翟城村自治模仿自日本的村町(大概因为米迪刚曾留学日本),但翟城村人认为这些“皆属不知内情之谈”,翟城村自治的经验来自传统,包括吕氏乡约的精神,“多系按照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因革损益,量为兴作”。
发端于宋代的乡约,虽历经明清时代的异化,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乡党自治的传统上来。
版权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