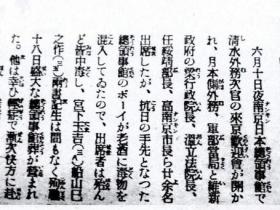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乱治交替,周期兴废。每个王朝,无论君主贤与不肖,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用黄炎培的话来说,谁也走不出这个周期律,道理何在呢?
自秦汉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官僚帝国。封建制自打春秋时期结束,就只有短期和局部的复辟,不再有整体的存在。这样的帝国,无论大一统还是南北分治,或者多国共存,每个政权都是官僚型的帝制。帝王与官僚共天下(朕与二千石共治天下),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所以,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个最核心要素。皇帝的统治能力和官僚机器,以及制度的有效性,一般来说,是帝国兴衰的关键。
皇帝的胡来,可以导致帝国的溃败;同样,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二世而亡的王朝,比如秦与隋,是皇帝折腾的结果;而西晋的速溃,则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另外,明代类似的制度问题也导致了动荡和王权的更迭,只是因为发生在朱氏家族内部,人们不将它算作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两者比较起来,官僚机器的分量其实更大。一般来说,只要皇帝不特别的瞎折腾,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则王朝一天都活不下去。当然,官僚机器整体罢工,发生的概率不大,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是老化。
平稳传递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就像一台机器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机件老化。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更大的难题是,在古代帝制条件下,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修补,顶多更换零件(人),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即使还能维持,但再往下走,就无论如何都不行了。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其亡也忽”的道理就是说,王朝会出现“老死”的现象。这种“老死”的现象,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
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有其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送往迎来的,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有其用,才设置机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究其实质,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拿薪水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
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而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像北宋那样——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活动,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一个事情被多头负责,互相牵制,搞的结构叠床架屋,除了养人别的什么事也做不好,就别的王朝来看,机构膨胀、效率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机构碍于祖制,无法明目张胆地扩张,编制外的胥吏就会大规模膨胀。养人养在官,养在吏,其实都差不多。
一个官僚帝国,官权在民间的制衡是有限的。地方的豪族和大户,或者我们后来讲的士绅,的确对于地方官的滥权有一点制约。但地方官只要执意胡来,士绅的抵制也大抵限于自保;能够通过关系将之拿下的,毕竟是少数人才办得来的事。如果朝政昏暗,地方官来头大,那么地方豪族大户、士绅可能连自保都难。至于一般百姓,地方官生杀予夺,只要没把事闹得太大,遭遇御史弹劾的可能其实不大。地方官和他们的下属,包括书吏和衙役,对于境内和过往的商人,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所以,借官权生财,在那个时代,是人世间所有行业中一种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无论官员是否贪恋他的官职,都会给他带来钱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不是讽刺“清知府”的贪,而是说,即使“清”,也一样会有这么多薪水外的收入。
在帝制的历史上,一尘不染的清官不是没有,但这样的人在任何朝代,都是罕见的稀罕物,比例之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多数朝代,官员的俸禄都是比较高的,靠俸禄就可以活得不错
(虽然他们未必就不贪腐);有的朝代,实行低俸制,等于就是让官员靠额外的灰色收入发家致富。地方官不消说,属于“亲民之官”,可以直接盘剥获利;负责主官不消说,就连杂佐官,只要能管点事,都很“肥”。即使不怎么贪,经手的财物也可以让手“沾油”。中央的官员可以通过中央地方之间的各种公务往来,让地方官给他们“纳贡”;即使是没有资格给地方官办事的京官,一样可以通过“打秋风”的方式,让地方官“出血”,有所沾濡。地方官进京公干,一般都得不停地掏钱——一方面,对所有用得着的高官进贡孝敬,按这些官员的级别和分量意思意思;另一方面,得不断地招待同乡、同年,给人塞红包。通过这样的互通有无,官僚群体自我的勾兑,使得官员这个群体,整体上被这个体系养着,皆大欢喜。
明清时代的胥吏,其薪水或者补贴低到几乎不能养家的地步,但这个群体却一直在膨胀。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正经八百的书吏和衙役数量未必会增加很多,但临时工却总是在增加,速度和规模还相当得大。以衙役而论,除了正役之外,还有帮役,帮役之外还有白役。一个县里面,最初的衙役只有几十人,但后来可以膨胀到几百,甚至上千人。尽管衙役在政治上属于贱民,人们依然对这个职位趋之若鹜,因为只要沾上官权,就可以借机弄钱。书吏和衙役本质上都是官僚机器上的部件,而且是很重要的部件,一旦缺了机器就会停摆。换而言之,他们也是官僚制度这个“铁杆庄稼”养的人。体系不明令给薪水,但他们靠在体系上,就可以丰衣足食。
随着王朝的延续,各级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地在悄然改变自己的性质,从办事,变成养人。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渐进的——各个机构,办事的属性逐渐减少,养人的属性逐渐增加。无论何种机构,办事的功能都在退化。
一旦有急务,朝廷只好设置临时机构来处理,后来临时机构变成正式的,也不办事了,就再设临时机构。到了王朝末年,机构整体办事能力退化到一定程度时,这个机构对于王朝的生存不是在帮忙,就是在添乱。比如说,一个县的政府,原来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朝廷维持秩序,同时征收钱粮,给朝廷“输血”。这个县政府从民众那里弄来的大部分钱粮,开始是大部分上缴,小部分自肥;而后上缴的份额未必减少,但自肥的份额逐渐增加,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到了民不堪命之时,就会因人祸而出现生计问题,如果再遇到灾害,就会发生动荡。这种时候,朝廷要么拨款救济,要么派兵镇压,都会加重朝廷的负担。这时,这个地方的政权就不是在帮忙,而是在给朝廷添乱甚至“挖坑”了。
由于机构是养人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这些机构没有用了,也裁撤不了。明代的兵制,开始是卫所制,但后来卫所的官兵只能屯田,不能打仗,于是只好另设镇守制,招募雇佣兵打仗。但卫所却不能撤,一直保留到明朝灭亡。明代省级官员原来是布政使、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三驾马车”,后来发现这样的三权分立没法干活,于是在三权之上加派一个巡抚。在巡抚成为一省实际上的首长之后,其实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可以撤销了,两者的衙门(机构)也可以裁掉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撤不了。而且这种职权重叠、官员互相牵扯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将总督也变成实际上的地方官,总督比巡抚高半格,有些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和湖北,督抚同城——一城之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职能重叠、职权打架,但就是不能裁撤一个。更可笑的是,清代不预立太子,因此太子詹事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也不能撤,说是留着官职给翰林们做一个升官的中转站。清朝原来设有漕运总督,督办由大运河转运的漕粮事务,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内乱,原来的漕运之路被断掉,就实行了漕运改海道,这个庞大的漕运衙门已经没有用了,但依旧不能裁撤。
晚清的戊戌维新,在百日变法之时,并没有实行一丁点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仅仅裁撤了一些闲散衙门。比如撤掉了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撤了漕运总督;在京城,撤了詹事府、太仆寺等十几个闲散衙门。就政府效率而言,这样的变革即使在旧制度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于这样的改革,仅仅在京城就涉及万把人的生计,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为西太后刁难光绪,为难变法,提供了口实。尽管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权力二元结构,西太后担心变法提升皇帝的地位和人望,自己失去权力,但中国官僚帝制结构本身的养人难题,也是一种过于难过的关口。
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而且,在旧体制存在的前提下,体制自身很难做修补。中国的官僚帝制,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若要修补,前提是必须改变体制。多少代王朝自身的变法,都是针对官僚体系的问题。但秦汉之后,没有哪次变法能够完全成功的。王莽改制,不改新朝还能维持,一改反而葬送了自己。其余像唐朝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都是失败。砸人饭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旦改革涉及官吏的饭碗问题,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只有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因为没有动人、动机构,仅仅改革了税收政策——把此前非法的摊派,变成了合法的正税,简化了手续,在不太触动官僚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减少了因征税手续繁复对百姓造成的勒索。即使这样,张居正死后依然因此而遭到清算。官僚帝制框架下的官僚体制一旦生成,就有巨大的惰性,这个惰性就像天文学上的黑洞,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
过去历史上的改革难,改革者下场惨,本质上都是过不了养人难题的关口。
版权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