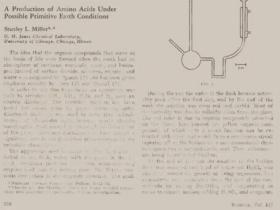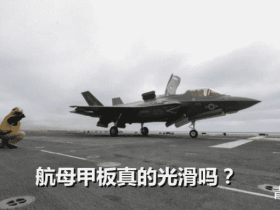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大夫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昔时的许多受试者终身饱受性病的困扰。
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大夫为了探求对抗性病的方法,在许多受试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接种、让受试者与染病异性性交等体例,让上千个危地马拉人感染了性病,而其中大多数人直到死去,都从未得到治疗……
那些针,是在没有提示或给出诠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脱离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饬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大夫经营的诊所报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大夫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如许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如今回想,他认为昔时的大夫是在有心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说,本身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偏远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大夫,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由于缺少资源,我一向待在老家,试着本身治好本身,”拉莫斯说,“感谢天主,我在有些年头会感觉好点,但接着就会复发。”曩昔几十年里,他常常会在排尿时痛苦悲伤流血,他的病还传染给了妻小。这些,都是他接受《天然》杂志采访时吐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透露表现,他也是一辈子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他的妹妹一出生头部就有溃疡,后来一向脱发。拉莫斯和他的后代都把美国看作他们几十年饱受性病之苦的祸首。“这是美国的一项实验,目的是检验性病对人的危害。”本杰明说。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STD)的实验。昔时,美国当局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偕行一路,在未经赞成的情况下,对5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性工作者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偶然还行使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当局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昔时的事件睁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透露表现训斥,说昔时的实验“可恶”、“可憎”。2011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透露表现:“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背,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熟悉,以及昔时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效果也是如此。”
不过,假如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昔时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撑,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认为本身做的事情特别很是紧张,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如许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们晓畅,本身的研究不受社会上某些人士的待见。但在他们眼里,这些研究在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信赖研究效果会带来广泛的好处,能帮助危地马拉改善公共卫生体系。这种种托言,都对今天的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提出了警示。
1
反梅毒战争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的卫生官员都忙着和性传播疾病作战。1943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分会主席的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估计,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35万。为了解决这个题目,美国当局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花了很大力气。
参与这场反性病战役的许多人后来当上了卫生高官——日后批准危地马拉实验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en),昔时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负责人,还就这个题目写了两本书。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经费办公室,而该办公室在1946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经费支撑。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透露表现,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特别很是活跃的性病分部”。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实了青霉素能有用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很多疑问。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庖代相沿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软膏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但痛楚费事,而且不怎么有用。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亟须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正当性和道德性睁开了争吵,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志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衔命开展实验的大夫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卒业。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想以此引起感染。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然而,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用感染受试者的手段,缺少了这个至关紧张的步骤,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不到十个月,实验就被停止了。
2
被囚的人群
在特雷霍特的尝试之后,研究者开始规同等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感染受试者,详细方法是让他们和已经患病的异性性交。
1945年,一名危地马拉的卫生官员在VDRL工作了一年,在此期间,他自动要求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这名官员叫胡安·富内斯(Juan Funes),是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的负责人,是帮忙研究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危地马拉,卖淫是正当的,当局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诊所检查、治疗两次。富内斯负责一家大型诊所的监管工作,可以保举得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参加美国的实验。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发起,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并获得了110 450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方面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蓄意传播性病,明确违背了当时的危地马拉法律。但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次政治动荡,该国官员对美国的计划并不反对,像危地马拉公共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甚至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赛·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难逃相干,他对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开展梅毒研究一事,至少是有所耳闻的。对危地马拉的官员来说,美国的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行使美国的资金来进步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引进先辈的科学技术。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达危地马拉,开始筹备实验。他的计划是先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然后检验青霉素和一种名叫“orvus-mapharsen”的药剂的防病结果。起初,科特勒行使染病的性工作者来向士兵传播淋病,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资料表现,有一名性工作者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此外,研究人员还行使性工作者在一所监狱内开展了研究。
可是,用这种“天然”的方法来造成感染也不容易,于是研究人员改用接种法。他们用带病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或者用一根牙签将溶液送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在危地马拉的国家精神病院,科学家在男性病人接触病原体之前先将其阴茎划破,以此增长感染的机会;他们还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据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科特勒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但委员会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有些实验在精神病人、囚犯和武士之外,还用到了孤儿和麻风病人,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中诊断测试的正确性都进行了测定。
委员会透露表现,没有证据注解科特勒在实验时获得过受试者的赞成,虽然有几次他的确获得了军队长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院大夫的允许。在一封写给他的上司、VDRL主任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信中,科特勒坦率本身对精神病院的病人有诳骗举动,目的是给他们注射梅毒,然后治疗。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称残忍。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细致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大夫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这时,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尿道里流出鲜血,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提议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还为陆军制订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司为当地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大夫和技术人员。另外,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报告监狱研究时写道:“对方很迎接我们的团队,无论是监狱管理人员照旧囚犯都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而这些东西是他们曩昔所没有的。我们因此觉得,这个治疗项目是值得的,也是完全合法的。”
到最后,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部分缘故原由是,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昔时12月。那年年底,他脱离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宣布了部分验血效果,但科特勒没有宣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背,而且在筹划和实行上都十分糟糕。
3
显赫的职业生涯
虽然经历了种种失败,但科特勒的履历倒是由于这些研究变得光彩起来。回国之后才几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带队去印度,引导对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上世纪60年代,他又前往阿拉巴马州,在污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中做研究带头人——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几十年,却始终没为他们治疗。科特勒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又在匹兹堡大学当上了国际卫生教授。2003年,科特勒逝世,而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还要等到很久之后。
迈克尔·乌吉安(Michael Utidjian)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匹兹堡大学工作,曾和科特勒合作过两篇论文。据他描述,他的这位前同事对性病研究相称尽心,对国际研究也很有热情。“在印度,他用青霉素治疗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拓荒了一片新的寰宇”,但乌吉安也透露表现,科特勒是一位有瑕玷的研究者,“我觉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卓异”。两位科学家合作检验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结果,但实验相称糟糕,效果“没有什么价值”。
在危地马拉,那些受试者的了局比科特勒凄惨得多。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昔时的受试者拉莫斯已经皮包骨头、举步维艰,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加上牙齿掉光,更叫人难以理解。他说,他一向拖到大约十年前、痛得无法小便时才去看病。他的儿子将他紧急送往医院,大夫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冈萨罗·拉马雷斯·蒂斯塔(Gonzalo Ramirez Tista)和拉莫斯居住在统一个村子,他说他父亲塞尔索·拉马雷斯·雷耶斯(Celso Ramirez Reyes)也曾在军队服役的三年里参与那些实验。那些科学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还给他打几针,没过几天,他就发现本身的阴茎里流出了脓水。“他脱离军队时还有那样的症状,后来还传染了我母亲,”蒂斯塔说。退伍后的雷耶斯饱受淋病的困扰,身体溃烂、视力降落,而且容易困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蒂斯塔也对美国当局提出了赔偿诉讼。他和拉莫斯都无法用档案支撑本身的主张,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维纳(Pablo Werner)大夫仍对这两起案件睁开了调查,效果发现,拉莫斯和雷耶斯的叙述,可以由他们的参军时间和他们提供的病例细节得到证明。另外,科特勒曾在论文中列出一份档案,调查人员据此整顿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4
永不再犯
2011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当局建立一个一样平常性的赔偿机制,为那些在美国当局资助的研究中受到危险的受试者提供赔偿。2012年1月,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增强和人类研究有关的伦理培训。但控方对此并不写意,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举动,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本身违背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由于他们在特雷霍特性求过受试者的意见,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遮盖了本身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特别很是感爱好,他说过‘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人们对于伦理的熟悉正处于快速转变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而在德国的纽伦堡,23名纳粹大夫和军官接受了审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它们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赞成、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赞成的能力,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需要的身体和精神危险。
尽管如许严酷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比如1935年,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透露表现,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赞成就可以了。这一点,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当局官员的意见。再说,他的很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看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晓畅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赞成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后由于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驰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证据注解,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赞成参与实验。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到了危地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这种内外有别的征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效果发现2008年一年,就有几乎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每每较低,对法规的实行也不那么有力。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透露表现,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赞成或没有诠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
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赞成付出7500万美元的巨款,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在此之前,尼日利亚的当局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辉瑞在实验中举动失当,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赞成。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控告,也不承认在实验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盼望、完全漠视其伤害的病人。莱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她指出:“将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紧张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赞成书呢?’”
在格雷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牢记,本身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透露表现,在临床实验中,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分歧就出现了”。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很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赞成,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合法的、需要的;但对于子女来说,前人的蛮横又是那样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