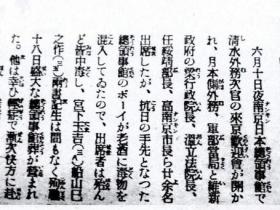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在那里,他看到了共产党领袖们的简朴生活: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他在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十年后的1946年9月,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蒂尔走进了延安。他采访十天结束后,当别人问起延安之行的感受时,他说:“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
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其行为和品质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官风正则民风淳”。抗战时期延安清廉的党风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老一代革命家陈毅曾赋诗赞道:“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各界名人的观感展现延安的魅力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尽管正面战场战斗惨烈,但节节败退,特别是溃退,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当时的共产党武装只有5万人,其战绩却不乏亮点。例如1937年11月出版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就刊载了关于山西八路军“屡次告捷”的消息。因此,不少人开始到延安去寻找希望。著名学者梁漱溟于1938年1月专程到达延安。
梁漱溟此前曾与国民党军事学家蒋百里交谈过三次,尽管他听过蒋百里的“打不了也要打” 、“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等等说法,但他的心情还是:“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 缘”“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到延安后则感到“毛主席完全乐观,我是悲观的, 我听了他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得乐观了。”“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梁漱溟的由悲观到乐观不仅在于和毛泽东的谈话,也在于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说:“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曾长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还特意加了一段注释:“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而他在国统区的看到的则是:“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均见梁漱溟《我生有崖愿无尽》)
梁漱溟对这样的鲜明对比极为震撼,后来他经常谈到他的观感,时不时在言谈之间极力称许毛泽东,称其“天资高,天生豁达。”延安之行还加强了他历来的反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理念。后来对蒋介石推行的所谓“宪政”也嗤之以鼻。
陈嘉庚先生是侨居南洋的华侨领袖。他组织募捐了巨款,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3月,他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访问。到达重庆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战时首都弥漫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类的奢靡之风。于是他决定到延安去看看。
延安使他耳目一新。他感到延安和重庆是两重天。作为祖籍福建的他,还特地找华侨和闽南学生进行交谈,了解情况。在女大参观时,他约两位华侨女生到招待所来叙谈,不觉天色已晚,陈嘉庚问她们自己徒步回校是否惧怕,是否需要派人送一程,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有问题了。”陈嘉庚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陈嘉庚7月17日返抵重庆,于7月25日晚作了《西北之观感》讲演。谈到延安,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他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讲完后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陈嘉庚这篇演讲在重庆很快流传开来,使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感受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鲜气息。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陈嘉庚则回应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蒋介石于7月28日召见陈嘉庚。陈嘉庚语气委婉地规劝,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蒋介石听后声色俱厉地说“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
在随后巡视国统区各地时,一路见闻大都使他感到失望。他1946年出版的《南侨回忆录》有如下记载:
他对那些动辄摆宴的单位说,“余此次代表南侨回国,系工作职责,在抗战困难时际,凡可节省一分便当节省,勿作不必要应酬,致或有不便。随诚意设宴招待,然反使余不便,徒花许多费奚益。”
在考察滇缅路时,他发现车路管理仍腐败。“西南运输委此腐败之人,有意如此开销,彼必呈报昆明机关,欢迎某某费去至少千元,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车站陋习如此,西南运输安有成绩可言。”“当次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如此,可胜叹哉。”
在进入故乡福建省后,“余在南平,则有漳州两代表来迎,又有永春某君等,具报闽南民众,受苛政惨苦,有不聊生之概。余闻后以闽南既如此凄惨,闽北不知如何。询福州两代表亦略相同。”“余自到福州后,报界记者及此间访员,男女十余人,纷纷来言,此间民众苦景,而尤以贫民为惨,都由贪官污吏,种种苛政。”“市内贫民随如此悲惨,而茶楼酒店,日夜仍热闹不休,多系军政界公务人员花天酒地也。”
令他震惊的还有那些壮丁的悲惨命运。“九月二十七日,上午离南平,将往崇安县。甫行不远,见路旁有两死尸,其一全身无衣服。据同行宪兵言:‘该尸系壮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当平民,就被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故民众多有中年失踪者。’”“壮丁用绳索缚联,此为余亲见之。至于其他多样,如用铅线环于颈项,然后用绳穿在铅线,相联成对,与及铅线环于手臂,再用绳索缚之,此系余入省之前所未闻者,余未敢信为事实:迨今亲见用绳缚之事,乃信前闻不谬也。”
返回南洋,陈嘉庚在新加坡欢迎大会上,把归国的所见所闻作了介绍。在陈述完延安地区和国统区有如天壤之别的情况之后,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7月1日到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成员、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一行六人访问了延安。延安的山水、人物等万千气象都让黄炎培等人耳目一新。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没有看见茶馆,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短发,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黄炎培把这些观感都写在他的《延安归来》中。此书经过精心策划,终于冲破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发行成功,一时洛阳纸贵。他在书中描写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个“朴实稳重,沉静笃实中带着文雅,谈笑风生,随便得很,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毛泽东先生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
各界名人发表的观感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风貌。
国共交往扩大了延安的影响力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重新开始交往。这些交往大都扩大了延安的影响力,当然也就大大地增强了共产党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除了有抗战的目的外,还有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的目的。因为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
但八路军的一系列表现,特别是平型关大捷,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共产党武装刮目相看,他称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1938年4月17日上午,卫立煌以借道为名访问了延安,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到达后毛泽东就亲切地会见了他,双方洽谈甚欢。这一切都给了卫立煌意外的感动。当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感到非常新鲜、敬佩。延安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也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演讲时动情地说道:“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更多的变化。不久他批给了八路军大批军用物资;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收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卫立煌态度消极,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初设法逃出南京,隐居香港。1955年3月终于回到大陆,后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
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在这些联络参谋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的,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其中少将徐佛观的经历很值得一提。他不但多次与毛泽东畅谈过,而且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警示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有学者这样描述:“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
徐佛观1943年5月进入延安。初到不久,就对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在和朱德、叶剑英的谈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认为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他还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其他一些先后在国民党阵营工作过的人士,也对扩大延安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丘琮是台湾抗日英雄丘逢甲的儿子。他中学毕业后,即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矿冶专业。学成回国后,曾先后在大陆执教大学,从事实业,一度担任广东省政府的顾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丘琮为寻找抗日真理,来到延安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还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听课。他曾访问过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了解边区政权建设,了解各级政权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他访问过群众团体,了解怎样组织和教育群众,怎样建立人民武装,怎样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的。经过考察以后,他说共产党对日作战很坚决,而且有一套办法,最根本的是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是国民党做不到的,值得学习。离开延安前,他向毛泽东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敬意,并表示要返回广东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许。
丘琮回到广州后,通过做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部的工作,取得了第七战区少将参议的职衔。他利用这个身份,组织成立了“东区服务队”,运用从延安学来的经验,大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全民抗战,并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丘琮重返台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辞去职务,常以私人身份访日,在旅日侨胞中宣传爱国思想。
陈志昆是夏威夷的美籍华人。1934年,他的堂姐夫,时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夏威夷探亲后,带他回国担任了自己的英文秘书。在此期间,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陈志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高官有较多的接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孙科之托,带其两个儿子到美国就读。
回到美国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志昆牵挂着中国的战事。他迷恋上了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来当他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心灵受到了震撼。于是,1938年8月,他克服重重困难到了延安。
陈志昆进入延安就亲眼目睹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们纷纷涌向延安的热烈情景,亲耳听到了连绵不断的抗战歌声,亲身感受到了处处洋溢着团结抗战的蓬勃朝气。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不久他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幽默风趣,使他很快消除了拘束感。他们开始谈孙中山,谈孙科,谈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时局,谈美国……陈志昆把毛泽东与早已熟知的蒋介石在心里做了个比较,认为:蒋介石令人生畏,毛泽东让人敬仰。 毛泽东还为他题词鼓励他的抗日热情。
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告诉陈志昆“你要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就不是上前线去杀几个日本鬼子,而是回重庆去,告诉孙科这些人你的所见所闻,促进大家共同把抗战进行到底”。于是,陈志昆回到了孙科身边。他利用各种机会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介绍了延安的真实情况,后来孙科发现他受到监视,就安排他去和斯诺夫妇、路易.艾黎一起搞“中国工业合作社”(公合),以另一种方式支持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陈志昆和新婚妻子一道,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从1950-1961年那11年,我们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变化。”“虽然当时物资贫乏,但人的精神是充实的,思想更是纯洁的。至今我们还是说,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北京的11年。”晚年,他回到夏威夷,担任了当地华人华侨社团的领袖,为中美友好贡献余热。
无论是当时的各界名人,还是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他们实事求是的所见所闻一经传播,延安的形象就变得愈加光彩夺目;同时,延安之行也改变了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命运。
外国人眼中的“另一个世界”
自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后,就不断有外国记者和其他外国人造访了延安。他们的报道,他们的观感,逐渐使延安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一个亮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他的权威力作《中国近代史》中写道: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只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比较明显地例外。 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除了个人访问,还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团队访问。一次是1944年6月至7月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另一次是1944年7月22日到达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
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以后,美、英等国为了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当时的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战不力,军心涣散,士气衰落,美、英等国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为此,他们于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武装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尽管国民党一万个不愿意,但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不敢公开拒绝,只得表示同意。为了控制记者团,国民党将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等记者参加,安排国民党官员领队,并规定中外记者的统一行动纪律,最后在重庆组成21人的中外记者参观团。
外国记者结束延安之行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对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成绩做了翔实的宣传和积极报道。比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斯坦因1946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并先后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发表于美、英报刊,引起了各界良好的反响。
自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已对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因而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经过不断努力,1944年6月21日,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罗斯福总统关于派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的要求。6月23日,蒋介石被迫同意,但为了降低代表团的规格,把名称改为“美军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到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考察、访问。在此期间,他们发表了很多讲话,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主要成员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他在1944年7月28日第一次发回的调查报告中说:“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美国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在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基础上,于1944年11月7日写出一份新的报告。该报告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抗战时期的延安,党风正民风淳,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的共识。当然,无论是在那时,还是在现在,个别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亦不足为奇。例如当年的傅斯年和当代的高华。关于后者,著名党史学者金冲及坦率地指出:“他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想这对人看待问题确实会有影响。 高华的书出版后就寄给我了,当时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全部看,但我听别人说了大概印象。关于延安整风,他用的是公开发表的材料。延安整风核心的材料是会议记录,特别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等,很关键,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统地看过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他还是比较隔膜,很多是靠猜。”关于傅斯年和高华等学者看法中的值得肯定的内容,因为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赘。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抗战时期的延安社会也一样,但无可置疑的是光明面肯定大大超过了阴暗面,因而才有可能被万众瞩目。历史已经证明,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历史真相”问世,但一直无法撼动国内外史学界的基本共识。被称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权威学者的英国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其最新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依然认为,“延安和国统区显然在各个层面都截然不同。”“延安领导人朴素的生活和着装,街上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难民。”因而“普遍感觉‘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国家,正接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